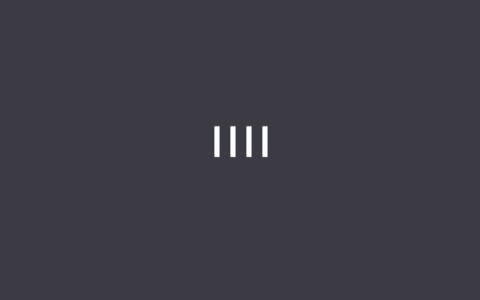[摘要] 本文概述民国时期同乡组织在公益活动方面日益增强的作用 ,并探讨其社会效能 ,包括关系网络 ,具有多重公共认同与组织关系的公众人物 ,以及民国时期广泛存在的呼声。通过南京国民政府以前及期间的几个事例 ,考虑不同时期组织型网络及其主持社会公益能力的不同情形。这些变化的情形反映了当时国民政府代理人物日渐把握和加强行使权力 ,以及青帮崛起与壮大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 民国时期 ; 同乡组织 ; 社会关系网络
不久前参加关于“民国时期的社会网络”的会议 ,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以前对于同乡组织与 同乡网络的研究。尽管民国时期这类的联系与忠诚几乎无处不在 ,它们却绝不是排它性的。实际上 , 随着城市福利事业与功能逐渐扩张 ,商业组织、秘密会社、宗教团体、私人慈善与政府机构等共同形成 网络 ,这多种成分并非完全对立互相竞争 ,反而多是平行发展 ,或有交集——同乡组织及其网络也是 这个网上的经纬与节点。本文将概要论述民国时期同乡组织在公益活动方面日益增强的作用 ,并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社会效能 ,包括关系网络 ,具有多重公共认同与组织关系的公众人物 ,以及民国时期广泛存在的呼声 ,即有社会认可的社会网络应该是公共的和服务于大众的。我将通过国民党南京政府 以前及期间的几个事例 ,来考虑不同时期下组织型网络及其主持社会公益能力的不同情形。这些变化的情形反映了当时国民党政府代理人物日渐把握和加强行使权利 ,以及青帮崛起与壮大的社会现实。
本文第一部分将简要描述民国时期同乡组织的社会福利活动。 第二部分将讨论一个超越同乡社 群界限、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的慈善机构 ,考察同乡组织及纽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第三部分主要考虑这段时期里社会网络的一个特点: 大多数同乡组织领袖的多重组织关系—— 许多人同时成为商界、慈善、市民或宗教界领袖。多重职位和它们带来的社会联系增进了这些个人的领导权威和行事效 率。我将通过五四时期和三十年代的两个例子 ,从每个时期“公众”政治的角度 ,考察这些同乡组织领 袖所编织的社会网络的社会涵义。文章最后将考虑民国时期社会与政治条件下同乡纽带与组织特别的适用性。
民国时期的社会福利活动
民国时期的上海同乡组织扩展了与晚清会馆相联系的慈善运动 ,并随着“公众”概念的变化 ,重 新定义了他们的社会福利事业。晚清的会馆为旅沪同乡提供灵柩寄放托运 ,周济穷困、资助慈善学校与医院也时有发生。民国时期的同乡组织则多数按现代的同乡会形式组成 ,财务和行政上有良好配备 ,可以为更多人数实行新的服务。
清末的上海会馆和公所的领袖在城市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因他们自认同乡社群阶层的 道德脊梁 ,也举办了很多保守传统、提倡道德的社会福利活动。民国时期 ,传统的慈善活动得到进一步发展 ,但又增添了一系列新式社会福利活动 ,对于道德展出新的理解。与早先社群的等级秩序相反,民国早期同乡会的社会福利项目强调更具民主性的民众主义 ,并在此过程中对慈善作了重新定义。当时 这种新的情绪经常在同乡社群内部权力斗争的背景下发生 ,正好反映了新旧观念和管理秩序上的冲突。 社群福利的意识形态基础与性质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改变。
广肇公所的例子可以揭示这个过程。1918年公所内发生保守派与“新式”革新派的分裂 ,后者要 求公所举办更大数量和新式的慈善活动。革新派希望通过将全部公所董事的捐助定期化 ,大幅度增加对旅沪穷困同乡的财政援助。他们还提倡将重点从有关丧葬的“消极慈善”转移到“积极慈善”上来 ,例如公所在慈善教育和医疗服务方面的投资。
广肇公所内革新派的策略包括发起群众大会 ,对公所内的寡头式管理有很大的冲击 ,在公所管理 的观念上出现了分离。他们召集了一个大规模的公众会议 ,宣布对富人募较多的捐用来周济穷人的计划 ,结果得到充分的支持而撤去了老公所领袖。革新派赢得胜利 ,掌握了公所领袖地位 ,并迅速成立了六所新的慈善学校。 大部分资金来自革新派商业领袖诸如霍守华、冯少山等的捐献。 通过这些慈善 活动 ,新同乡会领袖巩固了他们对于动员后的群众的恩主关系。另外还有几所主要的同乡组织也进行 了类似的变革 ,将他们的投入转移到现代市民福利方面来。
通过革新 ,广肇公所成为更广泛、更大众化的组织 ,公共福利活动的方向也发生改变 ,这些都是与当时上海出现的新的公众政治意识相联系的。新的公众政治意识产生于民国初期 ,并经五四运动时期 的大众民族主义而强化。自内部而言 ,旅沪团体从章程和公共选举两个方面重组了他们的管理结构。自外部而言 ,他们举办慈善活动、公共建筑、公众会议 ,在日报上刊登公告和会议记录 ,通过显示自己 的“公众”性而来巩固社会认可。从民国初期最大最有势力的同乡组织到那些较小些的组织 ,前者例如宁波同乡会 ,后者例如绍兴同乡会、湖社 (湖州旅沪同乡组织 ) ,它们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类似的转型。
民国时期同乡组织行政结构的扩展反映了它们所从事的活动中具有类同政府职能的性质。二、三十年代的同乡会章程中经常包含庞大的委员会结构 ,有各种专门的委员会来处理法律、公共建筑、住 房、调查、职业介绍、社会调查、学校、医院等等事宜。这些重组后的同乡社群所从事的新式社会福利活动在规模上有很大差别 ,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同乡组织领袖所拥有的经济与社会资本。福利活动的扩展也基于上海的商业发展。并非每个旅沪同乡组织里都有大的资本家 ,因此不是每一个在上海的外地人都能向他们的同乡组织寻求帮助。有效能的同乡组织要依靠财经资源和有影响力的领袖。因此 , 缺少这些经济和人事资源的旅沪团体常不能发展成可以巩固和扩展同乡纽带的组织。这些情形下陷 入穷困的外地人 ,很少或得不到同乡“安全网”的救援。
救援网络 ,同乡纽带与功能交叠的多重机构
随着同乡组织日益从事各种社会服务活动 ,他们的影响超出了同乡社群的范围 ,所组建的慈善团 体也不再基于同乡的定义。 同乡组织的这种活体性 ,及超越同乡群体界限发挥社会福利功能的倾向 , 或许可以从以下一个例子体现出来。我所指的是中国妇孺救济总会 ,民国初年在上海形成的一个面向 全国的慈善机构 ,由浙江背景的 3个同乡会组建而成 (绍兴、宁波、湖州 )。 总会最初设在绍兴同乡会。 宁波和湖州旅沪社群的领袖虞洽卿、王一廷也同时担任总会的首领。 当时上海妇女、儿童失踪或被绑 架的事件数量上升 ,引起社会忧虑 ,新慈善机构的组建正是针对这个问题。 由于这个项目常常牵涉到向遥远地区追寻下落 ,中国妇孺救济总会在当时不同城市有分支机构 ,而不仅限于上海范围。
由此可见 ,尽管总会仍然依赖同乡网络的情报 ,对不同同乡群体的服务程度也会有差异 ,却已经是几个同乡组织合作 ,提供类似全国范围内的市民福利。到二十年代 ,中国妇孺救济总会中浙江、江苏仍居强势地位 ,许多同乡组织的福利事务都结合了总会的内容。
二、三十年代同乡会记录显示 ,同乡会官员、中国妇孺救济总会及 (在三十年代 )的许多地方公安局之间存在、细致的协调工作 ,目的是保证各个事件中妇女、儿童的安全回返。 记录显示 ,涉案家庭成员一般不会直接求助警方 ,而是通常诉诸他们的同乡组织 ,由后者作为中介与中国妇孺救济总会及有 关的地方当局协作。也有直接诉诸中国妇孺救济总会的情况 ,如安克强 ( Ch ristian Henrio t )所见 ,这 或许也是因为他们将总会看作“同乡组织的延伸” 。 1935年浦东同乡会每月处理 5至 20件此类案件不等 ,每个案件中都有浦东和上海家庭的孩子由于中国妇孺救济总会的活动而得救 (这里根据同乡会 的行政范围 ,上海被看作浦东的一部分 )。 有时浦东同乡组织也会经手其他籍贯 (例如绍兴 )人员的安 全回返 ,有关原因现在还不是很清楚。这些同乡组织的记录还载有他们对于中国妇孺救济总会的财 金捐助情况。考虑到联络涉案家庭 ,取得地方警局协助 ,寻访失踪人员下落 ,安排旅程送他们安全返家—— 这些都必然牵涉的协调工作 ,妇孺救济总会显然十分依赖同乡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来解决这 些复杂的案件。 如果一个地方的人没有有能力的同乡会 ,个人找回失踪家庭成员的可能要小很多。
多重网络与转变中的公众政治
民国时期的城市头面人物 ,许多都是同乡组织的领袖 ,并通常同时据有若干个社会职任。 由于自愿发起的类代表制的组织在数量和形式不断增加 ,同乡组织的领袖们的领导职务也相应增多。通过多 重公共领导职务 ,同乡组织领袖得以扩展他们的恩主网络 ,增加他们的拥众 ,扩大他们作为公众人物 的地位及社会干预的效力。 这些个人的社会网络越紧密 ,他们在各领域间斡旋、沟通和发挥作用的能力就越大。
不同时期的公众政治意识及对社会网络的公共理解发挥作用的结果和方式都不同。 两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一个取自经济相对繁荣、公共组织迅速衍生的五四时期 ,第二个取自三十年代中期。 两个例子都关系到多层次的社会网络及公共领域的建设。之所以选取它们 ,并不是因为两者是各自时 期有代表性的同乡组织 ,而是因为它们的一些特征 ,可以说明各自时期有关社会网络的形成、所存在 的问题。
我的第一个例子是关于 1918年广肇公所的革新者之一 ,汤节之。虽然他的领袖角色开始于广肇 公所 ,改革同乡组织其实只是他参与当时上海全城市民运动的活动的一部分。作为广肇公所的一名新 领袖 ,汤节之在当时不少上海市民机构的权力斗争中都很活跃。 他是商业公团联合会早期的领袖 ,该组织发起过早期的商人动员 ,是五四时期上海行动的一部分。他向上海总商会的精英和寡头体制提出 挑战 ,鼓动总商会的民主改革。当人数扩张后的总商会选举汤节之 (以及同是广肇公所革新派的冯 少山、霍守华 )为商会新董事后 ,他的主张有了成果。与冯、霍二人一起 ,汤参与了与此同时兴起的比较 底层运动“平民商会” ,即由较小商户和店主组织成各路商界联合会。到 1920年 1月 ,各路商界联合会 已经宣称拥有成员 1万户。 汤、冯、霍三人 ,和波同乡会领袖 ,以及四十一路商界联合会 ,也成为 1920 年 8月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的核心。 到 1921年 9月 ,新的各路商界联合会诞生 ,并选举汤节之为主 席。 由这个简短的描述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新崛起的同乡组织领袖与多个公共组织建立联系 ,并成为 高度公众化人物的过程。 通过 1922年汤节之卷入一场官司所引发的风波 ,我们也可以观察当时公 众对社会网络的理解、运用以及局限性。 由于一个叫席上珍的秘书在汤节之的办公室里自杀 ,汤被逮 捕并被指控欺诈了席的钱财。当时报纸对这个案件的报道很好地说明了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具有 的社会重要性。 在公共舆论的法庭上 ,与两个当事人相关的组织都发表宣言并采取行动 ,分别证明他们品德高尚、行止无亏。
首先在报纸上发表言论维护席上珍的是洞庭东山同乡会。很快就有其他团体加入 ,推动公众舆论 同情席上珍反对汤节之 ,这些团体包括席上珍的母校—— 城东女学 ,另外 2个女学 (博文女学 , 南洋 女学 )席上珍江苏老家的另外 3个旅沪同乡组织 (苏州同乡会 ,吴江同乡会 ,洞庭西山同乡会 ) ,一个 “职业女子联修会” ,和一个“女子植权公司” 。
有人对为席上珍提供公众证辞的组织网络发表评论 ,并同时质疑汤节之的捍卫者 ,指出公众期望 有关组织 (作为道德保人 )也应对汤节之的信誉发表声明。连日报载席汤案 ,可知社会上已视为一种重 大事件。 “… …今女界以及各团体已将有所 [? ]。 然汤之同乡及举汤为董事经理理事监察人……查此 事真相 ,以判汤之曲直……当护其机关之固有声誉 ,速驱逐此害群劣马。 若调查所得 ,汤竟毫无关系 , 或汤竟因仁而得谤 ,当必出面护其同乡及董事经理理事监察人之名誉 ,即间接卫 [? ]其机关自身之名誉 ” 。
这个公开质疑— — 要求相关组织对当事个人的行为进行调查、作证 ,并承担维护社会道德的责任 —— 得到了回应。在对汤节之的审判期间 ,那些在他迅速崛起成为公众人物的过程中由他费尽心力构 建的社会网络也出面 ,站在他的立场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 在第二场法庭听证会和法庭宣判之间 ,二 十四所公团的代表— — 包括同乡组织 ,同业公会 ,自治会 ,工人互助会 ,马路商界联合会—— 召开一个 各团体联席会议表示“激昂” 。会议记录刊登在上海的日报上 ,将汤节之描述成上海司法整体滥用的受害者 ,并宣布纠正司法以保护人权的公共目标。 有意义的是 ,与会者宣称他们的行动并不是只为了汤节之 ,而是出于更广泛的市民主张 ,“一振司法精神 ,籍保国际地位” 。
会议的名录反映了汤节之人际关系网络的力量与局限性。尽管汤节之有广泛的社会组织关系 ,但 都为期不长 ,汤的政治主张抱负和运动为他在这些组织里赢得了许多朋友 ,却也树立了许多敌人。 许多组织的领袖都是先聚集了个人财富 ,然后因为他们显见的资源被拥立到领袖地位 ,汤节之却不同 , 他有许多社会责任和事业 ,却没有与之相称的个人财富。 他担任领袖职位的若干个组织中 ,多个因他 的被捕引发了内部争议 ,例如总商会受到压力要就此事公开表态 ,但决定保持沉默以避免争议。 也有些组织领袖选择公开地站在汤节之一边—— 以他们组织的名义 ,但内部也有反对。有些组织的成员立即表示抗议 ,指出他们的组织作为整体并不一定支持汤节之。由于这些争讦 ,汤节之的一些支持者 (包括宁波同乡会的代表 )不得不将他们组织的名字从公开支持宣言中拿下来。虽然数目有所减少 ,第 二天还是有 20个组织发起一个司法改革运动 ,提出了一揽子改革计划 ,表明他们对市民权益而非个 人忠诚的坚持。
尽管汤节之的捍卫者们努力表明他们的行动是基于广泛的公众利益 ,汤的抨击者则对司法改革 运动背后的私人关系网络发起攻击。 在一篇题为“私谊不是公论”的文章中 ,一个汤节之的批评者指 出: 如果少数人为了“私交”而假借“公论”名义去向人示威 ,这分明是破坏民众的威信 ,凡属民众都应 该起来向这少数自称民众代表的提起严重诘问! “各团体为了`私谊’ 去搭救汤节之……决不能容他们 戴着`公论’ 的面具。 何况各团体的多数份子 ,未必各个都与汤有`私谊’ …… 那么要搭救汤节之…… 用他们个人名字出面好了 ,何必糟蹋多数人共有的团体名义呢?`社会柱石’ 式的慈善家死了……这个 死者真做过何种`公益’ 吗? ……各团体的多数先生们… …为什么被人拉了去送出丧都不开口呀? ”
这篇评论鲜明地指出这个时期社会网络的一个特征 ,即公共与私人忠诚之间的模糊界限 ,以及许 多领袖与他们本应代表的社团成员之间的矛盾。 这里我想转入关于多层次网络与公共政治的第二个 例子 ,也就是 1932年的浦东同乡会 ,它是随着青帮首领杜月笙的势力到达顶峰而崛起的。当杜月笙的 势力增长 ,浦东人—— 以及凡是能沾靠浦东身份的人—— 迅速动员 ,结成一个组织 ,并成为杜月笙势 力的受益者。杜月笙此时已经在一系列市民组织和合法的商业企业中成为显要人物 ,浦东同乡会则把 他推举到一个地方恩主的机构性地位。这个地位上的还有浦东出身的不同政治、教育与思想背景的领 袖 ,如孜孜推动职业教育的黄炎培 ,棉花企业主和佛教居士穆欧楚 ,同是企业家 , 慈善家 ,佛教中人的 王一廷等。 通过服务于同乡群体 ,杜月笙无疑在名声上面受益非浅 ,此外还在同乡情谊的机构化中收 获了个人忠诚。杜月笙的显赫的确是促成浦东同乡感情复兴的原因。除开由李平书 1905年创立的一 个短暂、小规模的浦东同仁会 ,浦东的历史上并没有同乡组织 。浦东同乡会的成员甚至领袖也并非都 是浦东本地人。王一廷就是一例。他的祖籍在浙江湖州 ,但他出生在浦东。虽然传统上出生地与籍贯 并不一致 ,这个偶然的身世却使他得以享受两种同乡身份 ,并首先赋予这个称谓新鲜的、更加灵活和 策略性的涵义。
浦东人强烈希望与杜月笙建立合法联系 ,以运用他的影响力达成多种有用目的 ,这使得浦东同乡 会在其他方面也激发出类似的创造性。在 1931年就创立新同乡会发布征求会员宣言里 ,黄、杜、穆、王 就提出 ,与上海的其他同乡组织不同 ,浦东人不算外地人。“所幸吾人旅沪于故土 ,仅隔一衣带水 ,与他乡作客不同” 。然而 ,这并不妨碍成立旅沪组织 ,组织者们马上投入行动 ,建立了 73个以上“征求队” 来注册会员收缴会费。 部分“征求队”按常规的城区 (例如宝山县、南汇县 ,川沙县 ,等 )划分设立 ,杜月 笙则负责上海县的会员征集。但另外的“征求队”按“界”来划分 ,其范围反映了杜月笙遍及上海整个城 市的广泛的社会网络: 政党 ,军队 ,政府 (两队 ) ,市政府、交通 (三队 ) ,银行、保险、交易所 (两队 )、律师、 报纸、警察 (两队 )、中医、慈善界 ,以及各个主要的商贸业 ,包括杜月笙的贩卖水果的老行当。王一廷则 主持慈善界的“征求队” 。到当年 10月为止 ,这些队已一共征集到 54, 445元。到第二年 ,浦东同乡会 已经拥有将近 2万名成员 ,只比老资格的宁波同乡会略少一些。又过了几年后 ,同乡会征集了将近 60 万元 ,用以在 Edw ard II路上盖一座上海同乡会中最壮观的新式大楼。
浦东同乡会的领袖经常强调创立这个新组织是基于市民意识 ,即大同精神 ( univ ersality)。 比起 老的同乡会 ,“为全人类谋福利 ,不仅为一地之人类谋福利。善乎! ” 尽管浦东同乡会的提倡者强调这 个组织的公共与市民目的 ,三十年代的公众政治概念其实是围绕有势力的个人和讲求个人忠诚的社 会网络开展的。在浦东同乡会的例子中 ,我们很少能看到在有关汤节之一案的公共议论中那种对于为 个人忠诚穿上公众外衣的有保留态度。相反浦东同乡会到处都会标榜杜月笙。1936年新同乡会大楼 的揭幕庆典上 ,上海的各社会头面人物无论籍贯几乎全部到场。 庆典在新的杜亭举行 ,杜月笙和吴铁 城两人坐在台上 ,头顶是写着“杜亭”的牌匾 ,两个人之间是杜月笙的巨幅照片。 浦东同乡会的刊物封 面也是由杜月笙题字;凡有重大或疑难问题 ,往来交涉中都会提到杜月笙的名字。
即使这个标榜大同精神的浦东同乡会从许多方面看都是杜月笙的公共纪念碑 (他的广泛人脉的 确导致他的普遍重要性 ) ,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轻易忽略这个机构重要的慈善功能。 与其将浦东同乡会看作青帮首领的走卒 ,不如将它看作一个重要的慈善机构更准确些。同乡会依靠一个有着紧密社会网络的恩主 ,通过宣称拥有那些关系而获得它需要的资源。
浦东同乡会从事慈善的资源和效率的确引人注目。 1932年 1月 28日日本军队进攻上海后 ,浦东同乡会发出通知: 一切无家可归的浦东人都可以接受援助。 同乡会在周浦镇和杨思镇设立难民收容 所 ,并建立 6个施粥站 ,共耗资15540元。 1933年 9月台风袭击沿海地区 ,同乡会又筹得 366, 563元 的救济款。1937年 ,同乡会成立营救队伍和 12个难民收容所 ,这些收容所一直开办到1939年 3月 , 共收留难民 4, 186人。当战争扰乱市场 ,给浦东棉产区人民的生计造成灾难性的打击 ,同乡会成立 棉花贩运社 ,举资 100万元购买浦东的棉花 ,用船队将它运过黄浦江 ,储放到法租界安全的地方。
怎样看待同乡网络?
同乡组织所代表的社会网络极为灵活有用 ,且对于变化的环境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作为这种网络 的机构化形式 ,同乡组织持续存在了很长时间。晚清时期城市里的会馆和公所维护同乡群体内的秩序 (有时也组织抗议 ) ,在很多方面都行使了类同政府的职能。到十九世纪末期 ,则通过它们的商人领袖 , 形成城市内不同中国人群体间战略性的联系 ,有时也包括城市里的外国权威部门。 要建立同乡群体 , 将其中的等级制度合理化 ,社会福利是核心问题。随着中国宣布共和 ,同乡组织继续发挥重要功能 ,在大众民族主义和市民权运动为代表的社会运动中充当信息、组织和动员的载体。在发展中的“公众”概念背景下 ,同乡组织的领袖受到越来越多的压力 ,不仅要接受更多的旅沪同乡入会 ,还要通过公益活 动照料广义的同乡群体。
无论在民国初期政府职能支离不全 ,城市被分割成不同辖区的背景下 ,还是国民党南京时期的掠 夺性政府与对日战争的背景下 ,这些组织的福利功能部分地 ,也是不均匀地 ,弥补了国家政府的缺陷。 在当时的情形下 ,维护社群网络—— 无论它们从哪里获得资源—— 对于旅沪社群及其领袖都是有益 处的。在国民党南京时期 ,政府日益腐朽、残忍、冷漠和压榨人民 ,同乡组织在保护各自的旅沪社群、谈 判、有时向政府代理人据理力争等方面起到了作用。
同乡组织对于维护上海社会秩序的根本重要性 ,最明显体现在战争时期 ,如 1937年 8月虹口、闸北惨遭轰炸时 ,同乡组织弥补了上海市政府有限的处置能力。 21所同乡组织立即动员他们的资源救助各自的群体。除开此前提及的浦东同乡会 ,广东同乡会举办了 5个难民收容所;宁波同乡会开设了14个 ,并且组织船只 ,把 20万人转移到宁波 (占当时全上海宁波人的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二之间 )。 在 这个生与死的当口 ,当在上海的生活过不下去的时候 ,同乡纽带为许多上海居民提供了可以投奔的另 一个家。如何划分和理解这些网络和组织 ,这仍然是个问题。不同于社会网络的许多其他基础 ,同乡 纽带并不提供明确的信仰依据 ,也不阐发某种意识形态 ,不像群众运动 ,政党或宗教群体。因为唤起对 地区文化和外地人处境 (失去了家乡的正常关系网络的保护 )的共同感受 ,同乡感情为形成社会网络、 提供社会援助提供了可能。 同乡组织并非阶级组织 ,也不受职业限制。
如果说同乡纽带对于相关社会活动非常关键 ,很多情况下 ,正是由于它的涵义的相对空泛 ,这种 纽带变得特别有用— — 因为它可以被用于各种用途或与其他组织关系相结合。 由于同乡纽带能带动 许多大规模的群体 ,并联接社会各个阶层 ,同乡组织作为民众运动动员的载体极为有效 。当时的社会 存在着一个问题 ,即如何代表人民和公众的权益 (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都不同形式地存在着 )。在代议 组织和政府体制缺席的情况下 ,同乡组织 ,由于其数量众多 ,成员广泛 ,有时能形成与“人民”的概念非 常近似的群体 ,而这正是当时许多人苦苦寻求的。
尽管正式和非正式的同乡纽带交织在城市社会中 ,它们却不一定自动地形成网络: 只有当它能使 相关人等共同受益 ,才成为网络。这一点要依赖于等级制度和恩主的社会关系与资源。即便当这些组 织的接收的成员越来越广泛 ,大众主义的、有时甚至是民主性的说法逐渐增多 ,情况还是一样。在三十 年代 ,同乡组织与国民政府日益互相渗透 ,同乡组织的领袖则不仅收纳商业领导 ,有些情形下甚至接 受最有势力的帮派首领。这样一来 ,这些组织的社会性质及所依赖的权力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尽管很 多方面都令会员受益 ,并在当时日益压抑的政治环境中为市民权运动提供出口 ,三十年代的巨型同乡 会在本质上是些保守的组织 ,它们依赖现状。 只有现状 ,才是这些多重身份的同乡领袖保持财力和影 响力的基础。
【本文作者】:亿闻天下网,商业用途未经许可不得转载,非商业用途转载注明出处原文链接:https://cqsoo.com/ruanwen/21470.html
【版权与免责声明】:如发现内容存在版权问题,烦请提供相关信息发邮件至 kefu@cqsoo.com ,
并提供相关证据,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涉嫌侵权内容。反馈给我们
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本站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